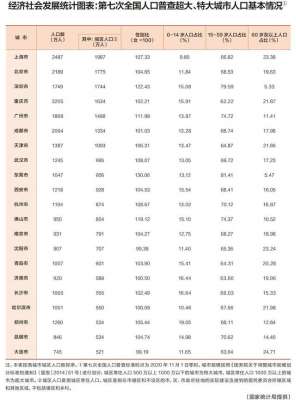迈蒙尼德(夭折的和平:后奥斯陆协议时代,巴以冲突缘何失控?)
来源:峰值财经 发布时间:2023-05-04 浏览量:次
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称,自冲突爆发后,加沙地带有近450栋建筑被摧毁或严重损坏,其中包括六家医院和九家基层医疗保健中心。冲突导致52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运营的学校收容了其中约48000人。
作为一个愤怒的民族国家的以色列再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般的丛林法则展示到国际社会眼前,作为抗争者的巴勒斯坦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附属在大国博弈与族群冲突下的绝望与悲情。而这一切的起因来自于5月7日以来,以色列在东巴勒斯坦地区强行拓展犹太人聚居区并驱逐巴勒斯坦居民。而巴以领土纠纷,我们可以诉诸于帝国解体时,抽身而去的仓皇身影,也可以追溯到1947年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的语焉不详,不变的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的对立。民族冲突与地缘竞争以另一种形式改头换面提醒着我们,我们并未告别弱肉强食的政治逻辑以及族群和解的困难。
然而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我们发现巴以双方的和解并非完全是天方夜谭。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达成的和平协议,使许多人看到了和平和弥合历史伤痛的机会。然而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却指出《奥斯陆协议》的天然缺陷,“以色列在签署奥斯陆协议时,是否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民族?奥斯陆协议是否彻底改变了犹太复国主义对“非犹太人巴勒斯坦人”的意识形态?这些协定是否保证恢复持久的全面和平?巴解组织的现任领导人是否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和民族愿望?”历史却如同萨义德所预感的一样,以意料之中的方式裂解。同样在奥斯陆协议破产之后,巴以双方都以一种相似的冲动向冲突的方向狂飙突进。我们今天在国际新闻中所见到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和平破裂后的短暂期间找到今天的对应物。

《敌人与邻居》,作者: [英]伊恩·布莱克,译者: 王利莘,版本:新思文化|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9月
原作者|(英)伊恩·布莱克
摘编|英麻
和平刺客
1995 年 11 月 9 日晚,3 名巴勒斯坦贵宾驱车赶往加沙地带北部, 登上一架以色列军用直升机,从海边飞往特拉维夫的斯德多夫(Sdeh Dov)机场。他们在层层安保下被护送到附近的伊扎克·拉宾的家中, 向他的遗孀莉娅表示哀悼。亚西尔·阿拉法特穿着橄榄绿色的作战服,但没有戴标志性的卡菲耶,脑袋在相机的灯光下显得极其光秃宽阔。他坐在那位悲伤的女人身边,在束束鲜花前面喝着茶。奇异得如同幻觉的事发生了,阿拉法特展示了他非常有限的希伯来语知识。在短暂的飞行途中,这位巴解组织领导人拒绝俯望以色列灯光闪烁的风景,甚至连雅法的哈桑贝克清真寺著名的尖塔也没有看一眼,而是“ 一直低着头,不看左右……整趟奇怪的旅程期间都是如此,尽管这是我们一生中难得的机会,能够看看我们心爱的国家”。参与《奥斯陆协议》谈判的艾哈迈德·库赖从未问过阿拉法特,为什么他不想看到“ 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全景,但库赖推测,“ 也许他还记得这里过去的样子,不想看到如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阿拉法特因为穿戴黑色外套和帽子,没有被拉夫阿希街(Rav Ashi Street)拉宾的公寓外等候的人群认出来。这是他自 1967 年战争后执行抵抗占领的秘密使命以来, 第一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

阿拉法特与妻子苏哈·阿拉法特
5 天前,拉宾被一名犹太右翼极端分子暗杀身亡,这沉重打击了《奥斯陆协议》,也打击了阿拉法特向莉娅、她的家人和聚集在此的以色列人所称赞的“ 勇敢的和平”。这栋摇摇欲坠的临时建筑本就遭受着两边敌对者坚持不懈的猛烈抨击,刚刚又失去了两位有勇气建成它的领导人之一。当纳比勒·沙斯报告拉宾被谋杀的消息时,阿拉法特回答:“ 和平进程今日终结了。”
阿拉法特通过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要求参加葬礼,但临时接任以色列总理的希蒙·佩雷斯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了。但库赖代表巴解组织参加了拉宾在赫茨尔山(Mount Herzl)下葬的庄严典礼,在场的5 000 名悼念者中包括比尔·克林顿、侯赛因国王和胡斯尼·穆巴拉克。库赖事后回忆起以色列国防军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殷勤关切,他们曾将阿拉法特、法塔赫老兵马哈茂德·阿巴斯和他自己送往特拉维夫; 而这种飞机过去通常用于追杀巴勒斯坦战士。时代似乎真的变了。

刺杀拉宾的凶手伊加尔·阿米尔
犹太右翼极端主义者伊加尔·阿米尔(Yigal Amir)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王广场(Kikar Malchei Yisrael)一个支持和平的集会上射杀了拉宾,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这个来自海尔兹利亚的法学生两年来一直在筹划谋杀,有一次他已经拔出了伯莱塔手枪,想要刺杀总理,但在最后一刻放弃了。一年前,他还参加了希伯伦大屠杀制造者巴鲁克·戈尔茨坦的葬礼。以色列的政治气氛已然危机四伏,分歧严重。拉宾被描绘成头戴卡菲耶、身穿纳粹党卫军制服的形象,耶路撒冷一 次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主要发言人的反《奥斯陆协议》示威活动就是这样描绘他的。“ 人们高呼‘ 拉宾是婊子养的’‘ 凶手’,因为 他‘ 将国家带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口’‘ 与魔鬼阿拉法特达成协议’而辱骂他。”6 阿米尔是个孤僻的人,但他获得了朋友、支持者以及更广泛的拥护。极端主义的拉比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总 理的政策构成背叛,为了犹太人民的利益杀了他情有可原。11 月 4 日的枪击事件发生后,25 岁的阿米尔立即被拘留。他的镇定自若令调查人员惊讶,他甚至要了一杯酒—“ 一杯杜松子酒”—以庆祝“ 拉宾之死”。“ 我是独自听从上帝的命令行事的,我不后悔。”他告诉他们。
拉宾对恐怖主义并不“ 心慈手软”,也没有纵容阿拉法特。在谋杀发生前 6 个月,哈马斯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加沙地带杀害了 7 名以色列士兵,总理对此予以严厉制裁。阿拉法特理论上仍致力于打击伊斯兰主义者,逮捕了数百人,并一再警告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尊重奥斯陆协定。然而,无论他是不愿还是不能—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施以足够力度的打击,每次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似乎都遵循着一种明确的战略,为以色列强硬派提供着理由:7 月份在拉马特甘(Ramat Gan)杀死 5 名以色列老人的公交车炸弹事件,似乎有意选在奥斯陆谈判下一阶段完成的最后期限之前,引发了协商中的以色列与巴解组织间的危机。爆炸案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 的以色列人认为会谈应该中断,只有 37% 表示应该继续。法塔赫控诉不知名的“ 躲在新闻头条和口号背后的叛徒”阴谋阻挠以色列从西岸撤军和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之事。

法塔赫组织的战士
每次炸弹袭击都会招致以色列的惩罚性反制措施—大规模逮捕、宵禁,以及最重要的长时间关闭过境通道—这给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困难,减弱了人们从已发生的变化中有所获益的感觉。
但他们仍在艰难前行。1995 年 9 月,奥斯陆二号(Oslo II)协议在埃拉特附近埃以边境的塔巴举行的会谈中最终敲定。它规定了巴以在就“ 永久地位协定”进行谈判的过渡期间的双边关系。这份 300 多页的协议含有大量附件,涉及除东耶路撒冷外的整个西岸,以及一项循序渐进的以色列撤军计划。扩充后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当时已 有 3 万名警察和 6 个独立分支—负责“ 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暴力事件,防止煽动暴行”。区域协调办事处(District Co-ordination Offices) 也成立了。艾伦比大桥和拉法赫过境处的边境通道由双方各自安排, 巴勒斯坦方的正式管控是由穿制服的警察和国旗体现的,不过以色列一侧的情况被挡在了单面镜的后面。 协议中最夺人眼球的是建立“ 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政府”和巴勒斯坦议会的部分,人们得以首次展望选举的前景。
然而,更为重要的部分是其定下的领土安排。被占领土划分为三个区域:A 区由巴勒斯坦城镇和市区组成,占领土面积的 2.8%,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全权负责此处的法律和秩序;B 区包括村庄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占西岸的 22.9%,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要在此维持公共秩序,而以色列人保留了对安全的全面控制;最大的部分是 C 区,占领土面积的 74.3%,含有重要的农业区和水源,以色列人对这些地区的安全和公共秩序保有全面责任。这意味着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负责管理所有巴勒斯坦居民,但仅能完全掌控 2.8% 的土地。西岸和加沙地带被视为一个区域单位,但是有个至关重要的总体性保留条件—“‘ 永久地位’协商中将要讨论的问题除外”。巴勒斯坦人对和平进程的支持率正是在此时攀上了最高峰:71%。即使是在学生这个通常是巴勒斯坦人中最强硬的群体内,对谈判的支持率也从 1994 年 1 月的 44% 增加到了1995 年 8 月至 9 月的 62%,同期反对率从 47% 下降到 24%。 1995 年10 月,奥斯陆二号协议获得了 72% 的支持率,这是和平进程有史以来的最高点。然而在以色列,议会对奥斯陆二号协议的投票反映了逐渐 强硬的情绪:它在10 月初仅以61 票对59 票的微弱优势通过。“ 利库德” 集团宣称拉宾政府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签署协议,右翼对此怨声载道。“ 利库德”资深议员埃利亚胡·本—埃利萨尔(Eliyahu Ben-Elissar)称之为“ 以色列史上的黑暗一日”。不久之后,内塔尼亚胡参加了一个重申“ 忠于‘ 以色列地’”的仪式,并拜访了希伯伦的定居者,他同 情哪一方自然也就清楚了。整整一个月后,拉宾去世。
定居恩怨
从 1967 年起,尤其是自 1977 年“ 利库德”集团上台以来,定居一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而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由于以色列渴望在最终和平方案到来前确立更多既定事实,定居的重要性更是大大增加。1995 年 1 月,拉宾、阿拉法特和希蒙·佩雷斯获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后,拉宾承诺以色列不再建设新的定居点,且不会再没收土地,除了用于在西岸开通旁道,以分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并减少摩擦的土地之外。 然而没过几天—在拜特利德发生爆炸并造成 19 名士兵死亡后—内阁就批准在西岸建造 2 200 余套住房。东耶路撒冷的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总是被以色列人用特许或是变更排除在规定之外。这些公告似乎是故意挑这样的时间发布的。在耶路撒冷以南的贾巴阿布吉内姆(Jebel Abu Ghneim)地区—希伯来语中称为哈尔霍马(Har Homa)—建造 6 500 个住宅单元的计划也被公布出来。

西蒙佩雷斯 阿拉法特与拉宾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这片森林覆盖区位于该市 1967 年后单方面扩展(未获得国际公认)的边界内,是伯利恒及周边村庄巴勒斯坦家庭的热门野餐去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批评者认为,它在与伯利恒相邻的拜特萨霍内形成了一块天然腹地,因此这一在以色列国防军按计划撤出该城市前几周采取的举动具有挑衅性。“ 现在就和平”运动抗议道:“ 只有完全脱离现实的人才会相信,有可能建设这样一个巨型项目而不会对和平进程造成致命伤害。”整个 1995 年夏天,随着《奥斯陆协议》第二阶段临近, 定居者们开始更有底气地直言不讳,警告称他们会向巴勒斯坦临时政府的安全部队开火,与一切将以色列人赶出家园的企图做斗争。活跃分子占领了新的山顶制高点,在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周边搭建临时营地,将“ 绿线”内部的支持者整车整车地运送进去。7 月,一群右翼拉比,包括一位前首席拉比,宣布了一条哈拉卡古训,援引了 12 世纪学者迈蒙尼德的话语,即国王的命令若违背《托拉》,便可无视: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这意味着部队应该违抗所有撤离定居点的命令。这道律令遭到宗教界和世俗左右两翼共同的谴责,但备受定居者领袖欢迎。伊戈尔·阿米尔就注意到了它。奥斯陆二号协议没有对定居点问题做出明确承诺,仅是规定“ 在永久地位谈判得出结果前,任何一方都不得采取主动行动或任何措施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地位”。 但上述举动无疑违背了协议的精神。

拉宾与阿拉法特的世纪性握手
10 月下旬,萨尔费特(Salfit)作为 A 区的一部分,成为第一个移交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城区。该地位于纳布卢斯以西,在那里能够看见撒马利亚最大的犹太定居点之一阿里埃勒的红色屋顶。萨尔费特的以军指挥部被拆除,起重机移走了防御汽车炸弹的混凝土屏障、岗亭和钢铁大门,水泥地基也被连根挖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民政部总干事艾哈迈德·法里斯(Ahmed Faris)从军政府二号人物大卫·巴雷尔(David Barel)上校那里接手了这幢建筑。 杰宁、盖勒吉利耶和图勒凯尔姆紧随其后。12 月,以色列人在圣诞节前三天离开了纳布卢斯和伯利恒,最后离开了拉姆安拉,这个正在成为新兴巴勒斯坦实体(无论其性质如何)临时首都的城市。以色列的撤离给人们的感觉是,《奥斯陆协议》尽管存在缺陷,但重大变化正在发生。访问拉姆安拉的新民政部的穆里德·巴尔古提(Mourid Barghouti)表示,如今巴勒斯坦人在多年来屡遭以色列人羞辱的地方会得到热情接待。纳比勒·卡西斯(Nabil Qassis)是在高校工作的科学家,也是华盛顿会谈小组的成员,他说当时人们走来走去,看着穆卡塔区(Muqataa)以色列人曾关押和折磨被拘留者的空荡荡的牢房,感到“ 难以置信”。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与以色列人的权力
按照《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作用仅限于民政事务和内部安全。随着其整体逐步成形,权力从因提法达活跃分子转移到了自突尼斯返回的巴解组织官员手中,这些人通常是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自治政府的部长们往往是局外人,他们的副手则是曾在努塞贝的技术委员会工作的西岸或加沙人。法塔赫建立了“ 一个基于专制的阿拉法特领导的官僚阶层和地方精英之间盟约的类国家机构”,正如一名专家所指出的,“ 这些精英享受到了他们无法从以色列那里取得的东西—政府的奖励与政治庇护,以此作为他们支持当局的回报”。 以色列人对突尼斯返回者与西岸及加沙当地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了然于胸。
阿拉法特任命的地区管理者和市长里有亲约旦的人物,他们是广大起义者的死对头。在加沙,一位当地“ 名人”被委任领导法塔赫时,人们群情激愤。“ 领导层已经把那些为这项事业奋斗、为之牺牲的人推到了一边,”一位活动家愤愤不平,“ 我们拒绝让那些在我们的人民挨饿时住在五星级酒店、吃着鱼肉和巧克力的人成为领导人。真正的领导者是那些阵地上的人而不是酒店里的人,是那些在监狱接受教育的人。”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被法塔赫的忠实支持者所取代,这些人“ 以事情可能会对阿拉法特的政治地位产生什么影响来判断一切”。
这位巴解组织领导人复制了他在科威特、贝鲁特和突尼斯时的执政方式,像部落里的谢赫那样接见请愿者和央求者。一名观察家评论道:“ 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每个人,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有思想、有组织和有体系的人。”阿拉法特倾听了两百名权贵对加沙公路系统崩溃、排水及电力和电话问题表达的不满,但在会议结束时,这些人全都排成一列,挨个与主席握手合影,他“ 就跟好莱坞明星似的”。 他的控制习惯在财务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他人通通不能签署支票。 一名顾问回忆道:“ 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明白,安全、信息和金钱是领导力的基石。”阿拉法特的手段被巴解组织内部人士戏称为“ 法哈尼规则”,这是他在 1971 年到 1982 年在贝鲁特郊区的法哈尼总部磨炼出来的。他尤为关注“ 巴勒斯坦发展与重建经济委员会”(Palestinian Economic Council for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简写为 PECDAR),该机构是《奥斯陆协议》签订后由世界银行设立的,用于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提供援助。当阿拉法特任命自己为主席时, 担任委员会理事的杰出经济学家优素福·赛义格辞职了。萨利·努塞贝表示:“ 如果有流钱没有流入他的金库,他就会失去收买潜在挑战者的能力。”
巴勒斯坦解放军部队—其人员姓名曾受以色列人审查 —掌握着安全,吸收了“ 法塔赫雄鹰”(Fatah Hawks)、“ 黑豹”这类团体,为因提法达的忠实步兵们创造了就业机会,赋予了他们地位,尽管薪水微薄。许多被迫离开黎巴嫩并前往突尼斯和其他地方的人(及其家人)因此回到了巴勒斯坦。曾因 1967 年年底在西耶路撒冷一间电影院放置炸弹而入狱 10 年的法蒂玛·巴纳维(Fatima Barnawi)来到加沙指挥巴勒斯坦警察的妇女部队。在德哈伊什难民营,数十名曾经的囚犯被安全部队招募,另一些人则进入各个部委和机构担任文员、经理和董事,其中许多人过去是无业游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像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样运作,通过为一群感恩戴德的人提供铁饭碗来收买人心。“ 这对巴勒斯坦社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从头到尾反对《奥斯陆协议》的穆斯塔法·巴尔古提悲叹道,“ 人们开始为了工作和金钱互相争夺,因谁会成为董事、副董事、副经理,还有自己能赚多少而担心—因为这关系到大笔金钱,其中一部分来自外界资助,一部分来 自财政税收。” 新建的机关部委责任重叠且彼此矛盾,因此阿拉法特能够亲自干预并施加控制。“ 我们有领导人,”一位部长表示,“ 但我们没有领导层。”
1996 年 1 月举行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 88 位成员和总统职位的选举,是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合法性和受欢迎程度有限而无序的初次考验。“ 这片土地上从未举行过竞选,其事实上的统治者又是一个长期因不愿下放权力而臭名昭著的人,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不出人意料,”一名记者报道时称,“ 但随着竞选活动的进行,在大选中还发生了更令人不快的事情。”领导层选择将全国分为 16 个选区,并以得票最多者当选的方式选出代表,而没有采用可以按比例产生代表并 鼓励选民站在国家角度思考的单一选区名单选举制。反对者徒劳地 指出,这在一个家庭仍旧重于观念的社会中会助长宗族的垄断,阻碍 多元化和联合执政。政治学家哈利勒·什卡奇(Khalil Shikaki)评论道: “ 多数当选制可能适合稳定的民主国家,但它或许不适合存在深刻政治分歧且关于国族身份和领土边界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的社会。”
挑战阿拉法特的唯一候选人是萨米娅·哈利勒(Samiha Khalil), 而这仅仅是摆出个姿态而已,她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女权运动家,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奥斯陆协议》。议会竞选偏向法塔赫。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反对派发起运动抵制投票。独立候选人包含数十名心怀不满的法塔赫成员,他们不是没能在党内获得一席之地,就是被阿拉法特开除了。 纳比勒·沙斯、艾哈迈德·库赖和阿布·吉哈德的遗孀因媞萨尔·瓦齐尔(Intissar al-Wazir)等来自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高官在许多选区获得的选票都比当地人要多。 外国观察员大军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来自欧盟、日本、挪威、加拿大的团队等组成。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大增强了巴解组织领导层的合法感,这对于他们而言至关紧要。哈楠·阿什拉维这样高调的人物就是在其帮助下当选的。“ 阿拉法特告诉我,委员会中将会有大约 15 名女性,并补充说‘ 哈楠一个顶十个’,”卡特记录道,“ 大家都笑了。” 最终,投票结果的作用更多是巩固权力,加强承认,使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和平共处合法化,而非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大选某一日的民调显示,奥斯陆原则的支持率为 50%,只有 16% 的人反对。法塔赫获得了 57% 的支持率。
安全仍是所有问题中最触动人们神经的部分,同时也像以往一样,是以色列的重中之重。选举前几日,以色列人终于成功捕获了叶海亚·阿亚什,以哈马斯炸弹袭击出名的“ 工程师”。这名巴勒斯坦境内最大的通缉犯死于加沙地带的拜特拉希耶(Beit Lahiya),死因是一个为以色列人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给了他一部手机,手机里放置了爆炸装置。用监督了这场暗杀的“ 辛贝特”头子卡尔米·吉龙(Carmi Gillon)的话来说,阿亚什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他有“ 匪夷所思的生存能力……部分原因是他从未在一个地方待过一小时以上”。拉宾曾亲口告诉阿拉法特,阿亚什已经身在加沙,但巴解组织的负责人坚称此人实际是在苏丹。总理警告他:“ 我知道他在这里,如果你没有找到他并将他交给我们,我就会撕掉整份协议,包围加沙。”38 数十万人参加了阿亚什在加沙的葬礼,高喊着:“ 我们要公交车,我们要汽车。”猎杀行动在拉宾任上就已展开,但下手的许可是由希蒙·佩雷斯批准的。它遵循了以色列的传统:消灭最危险的敌人,不计后果。前一年的夏天,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什卡奇在从利比亚返回大马士革基地的途中访问马耳他,也被枪杀,杀手为据传是“ 摩萨德”特工的不知名枪手。

西蒙佩雷斯葬礼上的内塔尼亚胡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哈马斯卷土重来
1996 年 2 月 25 日,哈马斯展开复仇行动。在耶路撒冷,一枚装满钉子和滚珠轴承的强力炸弹在雅法路中央车站旁一辆挤满了人的 18 路公交车上轰然爆裂,致使 24 人遇害。另一名平民在阿什凯隆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遇袭身亡。伊斯兰组织称这是对杀害阿亚什的报复。不知是不是巧合,当时正好是巴鲁克·戈尔茨坦在易卜拉欣清真寺杀害 29 名巴勒斯坦人的希伯伦大屠杀事件两周年,这是对《奥斯陆协议》承受能力的一次早期考验。恐慌接连而至:一周后,又有一名哈马斯炸弹袭击者在耶路撒冷锡安广场附近登上一辆 18 路公共汽车,引爆了炸弹背心,造成 16 名平民和 3 名士兵死亡。翌日,一名炸弹袭击者在特拉维夫杀死了 12 人:在以色列最繁华的城市中最热闹的地段,也就是迪岑哥夫大街和乔治王大街(King George Streets)的交界处,遍地都是尸体。化为废墟的店铺的碎片纷纷落在汽车残骸上,茫然而恐惧的购物者张皇失措地冲出现场。几分钟内,这个交叉路口就挤满了警察和泣鸣的救护车。秩序还没恢复,以色列电视台就在跟进现场直播了。摄像机拍下了这些尸体的细节,其中有些衣服已被炸飞, 所有尸体都是烧焦的。还有一些令人揪心的孩童哭泣的场景,有些孩子还穿着为普珥节准备的漂亮衣裳。
这场前所未有的街头屠杀—8 天内有 60 人死亡—给以色列的政治和《奥斯陆协议》的未来打上了巨大的问号。佩雷斯渴望走出拉宾的阴影,凭自己的努力赢取权力。2 月初,他公开呼吁提前举行大选, 让以色列人第一次直接投票选出总理以及他们选择的政党。总理选举的获胜者将成为组建执政联盟的支柱。2 月中旬,佩雷斯鼓吹其政府取得的成就,将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描述为“ 欣欣向荣,不同于爱尔兰和波斯尼亚”。两周后,哈马斯的炸弹袭击者们也参与了竞选, 于是这种说法就显得难以服众了。“ 新中东”的说法—引发了对“ 好高骛远的”佩雷斯的讥诮嘲笑—从未显得如此空洞无物。这位民调支持率只有 20% 的工党领袖已经出局了。
以色列军队封锁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用宵禁和检查关卡施加旅行及贸易屏障,切断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辖的领土之间的道路,对哈马斯嫌犯发动搜捕。数以百计的村庄城镇因战略性布置的沟渠、沙土或石头路障而陷入瘫痪。自 1967 年以来,坦克首次沿整条“ 绿线”部署。在哈马斯获得过支持的地区,数十人被捕,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同样进行了无差别扫荡,而且有人指控他们对扣押的人施加暴行。40 已知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房屋被封禁,随即被拆除。

受到以色列“愤怒的葡萄”炮火袭击的巴勒斯坦居民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再次被迫中断在以色列的工作,自治区的经济损失惨重(据估计大致相当于国际资助者为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而给予或承诺给予的数额)。哈马斯各机构被关闭。以色列空降兵突袭比尔泽特大学及周边村落,冲进宿舍和公寓,围捕学生,并将他们一齐赶到足球场上进行审问,之后自治政府的警察在这所大学里遭人群投掷石块。数百人被捕。“ 我们不知道谁更针对我们,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以色列人。”从这次包围中脱身的 20 岁加沙学子“ 易卜拉欣” 抱怨道。之后不久,阿拉法特在访问拉姆安拉时遭到了更多的辱骂。 学生会选举中,“ 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联合参选,赢得了 52 个席位中的 23 席,而法塔赫只有 17 席。在拉姆安拉监狱,一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安全官员告诉一名被拘留者:“ 你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被分进了这三类人里头:第一类是以色列人想抓的人,第二类是政府想抓的人,第三类是为了安抚以色列而逮捕的人,你们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策划不久前的公交车爆炸案的“ 卡萨姆旅”二把手哈桑·萨拉迈在希伯伦意外落网,以色列人方才满意。这对佩雷斯来说是趁手的助力。佩雷斯还指责伊朗是一个遥远但冥顽不化的敌人,在投票日之前怂恿“ 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其他颠覆组织”袭击以色列。而在幕后,推进安全合作的力度已在增大,尽管在最佳时期也得处理一种棘手的关系—以色列人在面对巴勒斯坦任人唯亲、腐败无能的自治政府时那屈尊俯就、居高临下的姿态。巴勒斯坦人将哈马斯的壮大归咎于以色列的镇压,但佩雷斯和阿拉法特仍在开会讨论现状。佩雷斯明白合作是有限的。他解释道:
(阿拉法特)不能作为一个代理人存在。你不能命令他。你还不得不给他奖励。很多人问我阿拉法特是否值得信赖……他没有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会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领袖,也将一直如此。我们可以作为伙伴进行和平会谈, 但我们不能把他当成实现我们政策的工具。
工党领导人很快就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这次是在黎巴嫩南部, 以色列在长达 5 个星期的跨境交火中持续炮轰真主党据点,打击向北远至贝鲁特的目标。但在为期 18 天的“ 愤怒的葡萄行动”(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中,以色列的炮弹袭击了加纳(Qana)一个联合国基地,杀死了 108 名在一个集装箱中惊慌避难的平民,这一常规军事回应引发了深远后果。联合国的报告驳回了以色列声称这次屠杀是技术性错误导致的后果这一说法,于是黎巴嫩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暴怒回应变得合乎情理了。巴勒斯坦人自然与黎巴嫩受害者感同身受。然而以色列的批评家指出,以色列国防军给出了解释:它是在袭击南部的什叶派村庄,导致平民向北涌入贝鲁特,促使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遏制真主党。 5 月,民调结果显示佩雷斯领先 4% 到 6%,但在 5 月 29 日大选前两日仅领先 2%。以色列的阿拉伯裔选民—占选民总数的14%—响应社区领导人进行抵制的呼吁,他们谴责这位工党领袖是“ 儿童杀手”“ 战犯”。人们后来发现,72%的阿拉伯裔选民投下了空白票或废票。即便如此,右翼人士仍强调阿拉伯人对佩雷斯的支持, 将之作为反对他的一大理由。佩雷斯以仅仅 2.9 万票的差距败选。他口齿伶俐的“ 利库德”集团对手以口号“ 内塔尼亚胡,造福犹太人”进行活动,赢得了组建新政府的权力。
本文摘编自来源《敌人与邻居》。
原作者|(英)伊恩·布莱克
译者|王利莘
摘编|英麻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危卓
来源:新京报网